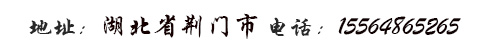宋朝不同身份的官员享有的医疗待遇
|
文官作为维持国家*务正常运转的重要人员,在疾病治疗方面,不同身份的官员享有不同的医疗待遇,因此在就医过程中呈现不同的特征。 一、中央官员的疾病治疗 中央官员位于都城,处于医疗资源最为集中之地,极具地域优势,求医问药十分方便。官方为符合具体品级规定的中央官员提供相应的常规医疗待遇。 首先,由翰林医官院等机构派遣医官为患病官员诊视。宋初便已规定凡文武常参官请病告过三日者遣太医诊视的旧例。 真宗景德四年作出遣医的具体品级规定,即凡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大将*、刺史已上、知杂御史、诸司使等请告三日以上者,由入内内侍省派遣太医诊视。 仁宗天圣年间又规定,在京的文武职事官患病者可经所在本司奏闻,以内侍领翰林院医官为其诊视。综合上述,请病告过三日且达到相应的品级规定才可享受官方医疗待遇。 实际上,中央官员在疾病治疗过程中也显现出因官阶高低之分所带来的差异。官员品级越高,越容易触及宫廷医疗资源。高级官员可得皇帝亲临问疾、宣医赐药等特殊的医疗照顾,而低级官员却无法享受此种待遇。 而宫廷所遣医官通常为医官之中的佼佼者。如元丰八年()四月,王珪感疾,皇帝下诏遣派国医诊视,并赐以御膳珍药。“国医乃名医中选”,医官经层层选拔而授,医术出类拔萃。 偶有特例,皇帝还将派遣多名医官为其诊治。可见高级官员所享受的宫廷医疗待遇十分优厚,名医、珍贵药材触手可及,皇帝宣医赐药也为高级官员增加了疾病痊愈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高级官员还可私下延请宫廷医官为其诊治。京师医官傲然难请,并非处于低级官员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内。如庆历元年()十月,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为母求医,言京师医官傲然难请,转而求民医。 而二十年后,即嘉祐六年欧阳修任参知*事时患口齿肿痛之疾,便“呼四医工并来”,未有纤效后又听闻王素有“蜀中真山豆根”,主动写信乞一二两。 可见官员品级越高,越易于延请医官。当医官医治无效时,在京官员还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来延请民间医生。而一般京官则没有皇帝宣医问疾、官方为其派遣医生的待遇,又难以私下延请宫廷医官,因此患病时需要依赖京城中的医疗资源。 二、地方官员的疾病治疗地方官员分散于各州县,自然无法与中央官员同享宫廷医疗资源,但偶有特例。如一部分守边之臣或有功之臣,虽不在京师,也可得皇帝特殊医疗关照。 至和元年()十二月,韩琦于知并州任上,上表请求仁宗差遣齐士明前去诊治病情,言其疾病“乘隙屡作,每妄攻而肆*”,以至于“实无意以求生”,仁宗遂派齐士明前去。 通常而言,地方官员可获得的主要官方医疗照顾来自于各地的驻泊医官、医学博士、医学教授、医学助教等人员。 医学博士、医学助教隶属于地方州县,驻泊医官又驻扎于各州府治所,“序位在州县官以下,非缘医药,不许与见任官往来”,反观之,如若地方官员有疾,征召医官也是情理之中。 如庆历元年(),宋夏好水川之战后,范仲淹知耀州,途中“眩转之疾”屡次发动,颇感“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便于“永兴*请医官看治”。 地方医官数量较少,且常有教习医学生或救助地方*民等其他职事。如此可见,地方官员所能依赖的官方医疗照顾相对较少,因此大多需要依赖民间医疗资源。 但宋代医疗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京城最足,其余次之,偏远地区更是缺乏医药。不少地方官员备受当地无医药之苦,毕仲游曾说:“关陕少医药,而多川陆之劳,良以为苦。” 若有医者治病有效,常被称为人生幸事。因此,在所处之地医药匮乏的情况下,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如何解决患病时无医药的问题十分重要。 首先,可向朝廷陈请合理的医药需求。如熙宁八年(),新任转运判官宋球便以“广南东路以瘴疠,近年数失监司”,乞求“增差医学邢慥”,神宗许之。 还可利用自身权力为医疗提供便利。或还可申请于某地寻医问药。其次,还可延请民间私人医生,另外,亲友帮助也是地方官员重要的医药来源。 在既无名医,又难得药材的无奈情况下,地方官员只能依赖自我救疗。如李复于夔州时,言夔州“他处药材皆不至,市无药肆,亦无学医者”,还曾写道:“予少亦留心于医,家人辈疾病未尝呼医,率多自疗。” 如此可见,因各地医疗资源不均,地方官员可利用的官方医疗资源较于中央官员有所减少,故多利用民间医生,无奈之下只能采取自我救疗的方式,偶有寻求巫医者。 三、贬谪官员的疾病治疗贬谪官员在处于缺少经济来源以及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其就医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官员一旦遭遇贬谪,首先经济状况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甚至还需亲友资助以度日。还将被迫迁居他处,有些路途遥远,需要长途跋涉。不但只代表远离中央,也意味着走进容易患病的地区,缺少医疗资源照顾的地区。 因而不得不承担着因仕途受挫几经贬谪所造成的苦闷心理,还须经受着由身体疾病带来的痛苦和衰弱之感。 部分偏远地区缺医少药,如苏辙被贬雷州后,又贬循州途中“风波恐惧,蹊遂颠绝。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官员被贬大多是因为朝廷中的*治斗争。“谪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顾”,贬官大多杜门省愆以减少交游活动。 此时若得亲朋好友帮助,必然是患难见真情。苏轼与程之才的事例为人称道。程之才为苏轼的表哥兼姐夫,但苏轼早年与他并无交集。只因苏轼的姐姐八娘原为程之才之妻,但却在夫家受虐待,又恰逢患病,而遭程家无视后死去,两家结怨。 但苏轼贬谪惠州期间关系出现了转机,两人冰释前嫌,且相谈甚欢,苏轼曾多次请求程之才为之寻药。贬谪官员在俸禄微薄、谪居之地缺医少药的处境之下,自我救疗被迫成为最主要的愈疾方式之一,偶得名医相助自然幸运之至。 苏轼谪居*州期间曾患臂痛,一日前往“螺师店看田”时,偶然结识名医庞安时,苏轼在庞家居住数日。庞安时不仅为其施针治疗,还赠送药物,疾病得以痊愈。 两人关系颇为亲近,苏轼又向苏颂推荐庞安时为其诊病,自言与庞安时“某颇与之熟”。与庞安时交游为苏轼治愈疾病提供较大的帮助;同时,庞安时也经苏轼宣扬而渐有医名。 医药匮乏终将影响到贬谪官员的生命延续。被贬官员死于谪地情况并不少见。天圣元年(),寇准卧病在床时,就曾作诗曰:“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不久便病故。 又如崇宁四年(),*庭坚孤苦病死于宜州,在此之前并无一人看望,只有在死后范廖为其经理后事,盖棺安葬于城南。 由上可知,贬谪官员因其特殊的*治遭遇,大多处于缺医少药之地,幸运者可得民间名医照拂、亲朋好友赠药等。当被贬至偏远之地无医药时,被迫进行自我救疗,更有客死他乡者。 四、致仕官员的疾病治疗宋朝规定七十岁为官员致仕的法定年龄,致仕后即意味着卸下自身职务脱离官场*治,以安享晚年。因此在疾病治疗方面与其他官员不同。 首先,与现任官员相比,官方对于致仕官员医疗待遇并无明确规定,患病后无须经官方派遣医官等繁琐程序证明自身疾病。 其次,可在自身经济条件允许下寻求医生诊治疾病,搜寻药材。现有研究中对于官员的致仕原因、致仕后的俸禄制度、养老生活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但对于致仕官员的疾病治疗问题尚未有专门研究,下文将对此展开探讨。 首先,官员致仕后无法享受官方医疗待遇,部分可得皇帝特殊恩例者除外。在唐代,就已有相关法令保障致仕官员的医疗问题,《天圣令》中唐令规定:“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致仕有疾患,在京城者,官给医药;在外者,亦准此量给。以官物市供。” 即在唐代,文武职事官致仕后无论在京城或在地方者,都由官方给予医药,但不同的是在地方上须“以官物市供”。而在天圣令中的宋令中却发生了变化,规定:“诸在京文武职事官病患者,并本司奏闻,以内侍领翰林院官就加诊视。 其在外者,于随近官司申牒,遣医为疗。旧外官出使亦准此。”可见宋代的变化有二,一是缩小了医疗保障对象的范围,未涉及致仕官员医疗问题,二是将提供医药的机构、过程明确化。 部分高官功臣致仕后还可得皇帝遣医赐药等特殊待遇。另外,致仕官员疾病治疗更为重要的特点在于脱离*治场域,不受官方制约,可自由选择就医与疗养疾病的地点。 现任官员如要到别处就医,需要申请经官方同意后方可前去,如建炎三年()三月礼部侍郎卫肤敏患病请就医于秀州,许之。若不经允准擅自前往,将受到惩罚。 依靠亲友及自救也是致仕官员治疗疾病的重要途径。皇祐元年(),范仲温即范仲淹的三哥,因二婿之事烦恼以致精神不振,范仲淹此时于杭州知州任上,从一张姓友人信中得知后,当即写信劝诫他安心养病,并送去“关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嘱咐他一定要服下。 这些原因部分致仕官员不得不熟悉并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因为自我救疗也是其常用的方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dougena.com/bdgjj/12433.html
- 上一篇文章: 41岁男子尿酸710,并发尿*症离世医生
- 下一篇文章: 西畴逐绿前行打造漠上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