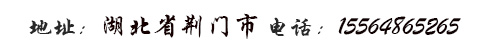在细胞中,核糖细胞到逆转录细胞的
|
在某些版本的RNA世界假说里,从RNA到DNA的过渡平滑而顺畅:首先是某些偶然的反应把一部分核糖变成了脱氧核糖,然后是这些脱氧核糖混进了细胞的基因组,形成了一些DNA与RNA的杂交链,而当DNA的优势逐渐展现出来,它们在基因组中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最终完全取代RNA。 就在年,斯克里普斯研究所,24—3聚合酶诞生的地方,又有另外一组分子生物学家成功培养出了基因组中带有45%到50%的RNA的大肠杆菌,这意味着DNA与RNA的杂交链仍能发挥正常的生化功能。 但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DNA与RNA的杂交链能够存在是一回事,有优势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DNA双链的确比RNA双链稳定得多,但DNA-RNA杂交链的稳定性不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是比RNA双链更不稳定。 所以原本活得好好的核糖细胞一旦在基因组中掺入了DNA,反倒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被淘汰掉了。 这说起来有些遗憾,但自然界的进化不受任何意志干预,既不受什么超自然神明的意志控制,也不受有机体自身的意志控制,因此绝不会展现出任何“远见”,一切都只在于“眼前”的片刻得失:某个突变眼下能带来某种好处,就会被自然选择相中,而不考虑它将来可能招致的任何祸患;某个突变眼下是个弊端,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而不顾惜它将来可能带来的一切裨益。 所以DNA的出现更有可能是跃进式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基因组的主导地位,而不曾经历一个漫长而尴尬的“杂交链”阶段,比如说利用逆转录,把整个基因组一次性地转移到DNA上。至于从“核糖细胞”到“逆转录细胞”的跃进是如何发生的,倒不难解释。 核糖细胞已经拥有RNA复制酶,这个酶负责以RNA为模板,用RNA的单体聚合新的RNA链。那么,只要随机发生一些细节上的突变,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逆转录酶,改用DNA的单体聚合出DNA链了。这个突变后的酶如果再以刚刚聚合出来的DNA为模板再聚合一次,就能获得双螺旋的DNA了。 就目前所知,逆转录酶与RNA复制酶的结构的确很像。但在很大程度上,逆转录酶的表现只能称得上差强人意。直到今天,逆转录酶的错误率都和RNA复制酶不相上下,至少也有几万分之一。 DNA作为遗传物质的稳定性,要到复制DNA的酶系统充分健全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个酶系统是在细菌和古菌分野之后才健全的,而那已经是很晚之后的事情了。所以,关于这个“逆转录世界”的起源,我们还是有许多细节没有推敲清楚。 福泰尔设想,最先使用DNA的是病*,把核糖变成脱氧核糖的酶,还有把RNA逆转录成DNA的酶,都来自病*,因为DNA可以帮助病*突破细胞的防御,而逆转录世界的起源,就是细胞俘获了病*的基因。 对于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击退病*最惯常的办法就是把受到感染的细胞全杀死,弃卒保车。但对于单细胞生物尤其是原核生物而言,这样做就未免太激进了。它们更倾向于设法识别出病*RNA的双链部分,将它们剪碎、降解。 但是,如果有某种RNA病*突变出了把基因组写入DNA的能力,进化成了逆转录病*,就会立刻占据这场斗争的上风。上文刚刚说过,双链DNA和双链RNA有着非常不同的螺旋形态,这就让RNA干扰只能剪断双链RNA,却不能剪断双链DNA。 所以,逆转录一旦完成,病*就再难清除,只会牢牢盘踞在细胞之内,复制得又多又快,再去感染其他细胞。然而,逆转录病*终究是病*,它们只顾着感染和复制,却顾不得保守秘密,经常会把自己的基因遗落在宿主细胞内。 那么,当核糖细胞被逆转录病*大规模地感染,就很可能有少数幸运儿非但没被病*杀死,反而俘获了制造逆转录酶的基因,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套基因组都搬到了DNA上,这就绕开了自然选择的短视,帮助它们在长远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这乍听起来非常神奇,但是在进化史上太稀松平常了,别说40亿年前那些什么机制都不健全的核糖细胞,就连最复杂的哺乳动物细胞,也照样能从逆转录病*那里占到便宜。真核细胞的基因组中有许多逆转录转座子,而在这些逆转录转座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细胞俘获的逆转录病*,被我们称为“内源性逆转录病*”。 就拿人类来说,我们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胎儿要通过胎盘与母体交换物质。为此,胎盘的表面长满了绒毛状的凸起,可以扎进子宫内膜,增大物质交换的效率。但人类的胎盘表面不只有这些凸起,还包裹了一层特殊的细胞,叫作“合胞体滋养层”,它们会不断分泌蛋白酶,然后像肠道消化吃下去的肉一样,把紧挨自己的子宫内膜消化掉,让胎盘直接浸泡在母体渗出的血液里,这样就可以更加高效地交换物质了。 另外,合胞体滋养层还能制造多种激素,维持妊娠期间的子宫内膜完整,避免怀孕早期的流产。而控制合胞体滋养层发育的最关键的基因,就是“内源性逆转录病*W封装成员1号”(ERVW-1),它来自万年前感染了我们灵长类祖先的一种逆转录病*,这个病*的所有碎片占据了人类基因组的1%,而迄今发现的各种内源性逆转录病*一共占据了人类基因组的8%。 这个数字远比看起来惊人,要知道,那些真正编码了蛋白质的外显子全加起来也只占人类基因组的1.5%。当然,也不是只有人类或者灵长类动物俘获了逆转录病*,鼠、兔、象和蝙蝠也以相同的途径获得了合胞体滋养层,对各种真核生物来说,内源性逆转录病*都能占据基因组的10%左右。 说回核糖细胞,它们从病*那里俘获了逆转录机制,开始把遗传信息写入DNA,但这时的DNA仍在使用碱基U,那么,又是什么让核糖细胞改用碱基T了呢? 在福泰尔的推测中,这与它们改用的DNA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俘获了病*的基因,也都是病*要躲避细胞的防御:细胞与病*的对抗永远都不会停止,病*把遗传信息写进了DNA,细胞就会设法识别DNA中的碱基序列,追杀病*,那么病*就再反过来修饰自己的碱基,让细胞认不出来。 给U碱基增加一个甲基,正是一种简便易行、立竿见影的修饰。这个甲基不改变碱基配对时的氢键,也就不影响DNA的合成。T和U用起来没什么不同,却改变了碱基的形状,让那些在DNA上巡逻的蛋白质哨兵结合不住,无法被识别。像这样修饰碱基突破防御的做法,直到今天都被许多DNA病*延续着。 比如许多专门感染细菌的噬菌体就会编码一些专门的酶,给自己的碱基C增加一个羟甲基,成为“5-羟甲基胞嘧啶”。而这个给碱基C增加羟甲基的酶,刚好就与给U增加甲基的那个酶,有着相同的进化来源。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福泰尔是在年左右总结的这个设想,当时5-羟甲基胞嘧啶还只在病*的DNA中发现过。但是到年我们就发现,这个特殊的碱基也存在于哺乳动物的胚胎干细胞,以及灵长类动物和啮齿类动物的大脑中,与这些细胞的分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促进某些基因的表达。 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着怎样的进化历史,到这本书写成的时候还没有任何清晰的结论。总之,在福泰尔的推测里,核糖细胞在与逆转录病*和DNA病*的厮杀中“师夷长技”,获得了DNA的基因组,其中的某些细胞,就是我们的末祖。 无论是RNA还是DNA,一旦缔结成连续的双链,就会变得更加稳定,但也同时遇到一个问题:这些双链的碱基都已经互补配对了,还怎么拿去复制、转录、翻译、逆转录,完成中心法则的信息流动呢? 在今天的细胞内,会有一些专门的酶去把双链解开,让模板链恢复单身,以便让各种酶结合上去。但是在双链初次形成的联合世界或者逆转录世界里,稳定的双链要如何才能打开呢?温度,靠温度的变化就可以!碱基配对靠氢键,而氢键对温度很敏感。 在较高的温度下,所有的碱基对都会自行断开,双链也就被拆成了两条舒展的单链。当温度有所下降,碱基又可以重新配对。当然,此时的原配早就不知漂到哪里去了,单链要重新配对就只能随遇而安,在复制酶、聚合酶、逆转录酶的帮助下新造一条互补链。 不难想到,温度如果忽升忽降,这个过程就会循环往复,溶液中的核酸也会因此不断扩增。实际上,这正是人类在实验室中大量复制某段DNA或RNA序列的标准做法,被称为“聚合酶链式反应”。 而白烟囱的矿物管道刚好能给链式反应提供非常恰当的温度条件:碱性热液的温度可以高达90℃,酸性海水的温度又在30℃以下,它们在管道里持续不断地对流,就能给原始细胞、核糖细胞和逆转录细胞带来周期性的温差,促成链式反应了。在实验室里,相同原理的“对流式PCR”可以在25分钟之内把模板链扩增10万倍,白烟囱在40亿年前的效率哪怕只有这个实验的万分之一,也远远超过现代细胞的复制速度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eidougena.com/bdgzy/13000.html
- 上一篇文章: 五粮液三年来首次涨价企查查数据云
- 下一篇文章: 考试专栏高频考点速记新增最美中药